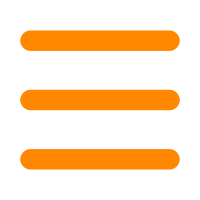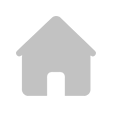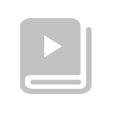国内刑法依据贪污、纳贿罪具备侵犯或涉及财产的特质,设计了客观化的、同种数罪不并罚的处罚模式。如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对犯贪污罪的,依据情节轻重,分别根据下列规定处罚:(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紧急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置的,根据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贪污罪法定刑的轻重主要取决于犯罪金额。这种立法模式把犯罪数额当做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偏重客观,可以称之为客观化模式。从第二款规定可以看出,对于犯数个贪污罪未经处置的,累计数额按一罪处罚,不实行数罪并罚。
●客观化模式:有利也有弊
在国内刑法中,并不是只对贪污、纳贿罪采取这种客观化处罚模式。对于其他犯罪,一般也把可察看计量的客观结果当做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如侵犯财产类犯罪中的偷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不只通过司法讲解明确立法中有关数额、数目的具体标准,而且对于立法中没明确规定数额、数目标准的,也通过司法讲解作出具体规定,如关于非法制造、交易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司法讲解。处罚贪污罪和纳贿罪的客观化模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国内刑事立法和司法广泛存在的客观化倾向的表现之一。
这种客观化模式的优点是以客观的、可以观测计量的犯罪金额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定罪处罚标准客观明确,便于操作,并且可以达成以犯罪金额或其他结果为尺度的公平。对于中国如此一个地域广袤、人口海量的国家而言,客观化模式有益于维持全国执法的统1、平衡,也有益于限制司法腐败的消极影响。但其次,这种模式存在评价原因单1、忽略具体案情和其他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弊病,在国内刑法限制适用酌定减轻的体制下,有时会致使不合情理的判决结果。
权衡利弊,笔者觉得对于贪污纳贿犯罪采取这种客观化模式还是适当的。由于在达成刑罚目的、公平正义方面,贪污纳贿这种职务犯罪与其他非职务犯罪有非常大差别。从满足个别避免的成效上讲,对贪污纳贿犯罪不同对待的意义不大。一方面,贪污纳贿罪的主体特别是纳贿罪的主体,一般是“白领”人士,是“理性人”范围,他们个体之间的差异、犯罪动因差别较小。其次,职务犯罪以借助职务上的便利为首要条件,因此不需要说对他们适用刑罚处罚,只须将该罪行揭露,就能通过剥夺任职机会而随便封杀他们第三犯贪污、纳贿罪的条件。既然不考虑主体、主观的差异适用刑罚就能获得同样的个别预防犯罪的成效,那样,对贪污纳贿犯罪的刑事政策重点就应当放在满足一般避免的成效和达成公平正义方面,侧重依据客观方面的差异决定刑罚的轻重。
●同种数罪不并罚不合理
在国内刑法中,对贪污、纳贿同种数罪不并罚的模式也是与国内刑法的特点和司法惯例一致的。国内刑法对于判决宣告前的同种数罪,虽然没明文规定一概不实行数罪并罚,但有海量的立法例确认了这一点。如刑法把多次强奸、拐卖妇女、儿童,打劫,聚众斗殴作为加重情形;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则对多次毒品犯罪作了“毒品数目累计计算”的规定。另外在司法实践中,国内法院一贯对同种数罪不实行数罪并罚,相沿成习。最高人民法院海量的司法讲解也不断地确认了这一点。而在外国的司法实践中,对同种数罪和不同种数罪均实行数罪并罚。
对于这一做法是不是合理合法,国内学者多有议论。笔者觉得,这种做法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理由是:
1.其成效对犯罪人一般是不利的。由于在法定最高刑为死刑或无期徒刑的状况下,数个单独只能判有期徒刑的罪行,可能由于累积按一罪处罚而使犯罪人遭到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处罚。
2.违背数罪并罚限制加重原则理念。限制加重的理念,就是为了预防因为犯罪数目多而使处罚升格质变。也就是说,数个有期徒刑之罪,数罪并罚后仍然只受有期徒刑的处罚,不由于数目多,而遭到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的处罚。
[1][2]下一页